|
11月1日,大连瓦房店市红沿河镇及周边的两万多居民,首次感受到当地核电站“送来的温暖”。这一天,东北首个核能供暖项目在辽宁红沿河正式投运,以替代红沿河镇原有的12个燃煤锅炉房,据测算,项目投产后每年将减少标煤消耗5726吨,减排二氧化碳1.41万吨。 作为清洁能源的核能,既可以发电,又可以供热。在“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”的方针下,今年以来,国家对新增核电项目的批准明显加速。9月13日,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了两个核电项目:福建漳州二期、广东廉江一期。此前4月20日,国常会核准了浙江三门二期、山东海阳二期和广东陆丰三个项目。迄今为止,中国今年已有5个核电项目、10台核电机组获得核准,为近14年最多。 根据《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纲要》,到2025年,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要达到7000万千瓦。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王寿君在8月举办的国际核工程大会上表示,预计2022~2025年间,中国将保持每年6~8台核电机组的核准开工节奏;到2035年,中国核电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将达到10%,相比2021年翻倍。 中国核电行业在蛰伏多年后,这一次真的要起飞了吗?核电安全的终极问题又该何解? 未来五年建设要避免“大起大落”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、国家核安全局原局长赵成昆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今年中国核电产业加速,除了技术积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外,在外部环境上,主要的“刺激”来自近两年极端天气频发叠加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能源危机。 他解释,核电在整个电力系统中扮演着双重角色。一直以来,人们一般更强调它的清洁属性,因为核电发电过程产生的碳排放量极少。 但也有一些国家坚持弃核,综合来看,如果仅从应对气候危机的长期目标考虑,核电在与太阳能、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竞争上不占优势。“但如果从能源安全的角度切入,核电的意义就变得不同了。”赵成昆说。 赵成昆分析,作为一种公认的“稳定电源”,核电的优点是发电稳定可靠,不像风光等新能源受外部气候环境影响较大。去年秋冬,当东北出现拉闸限电时,辽宁红沿河核电出力稳定,今年南方电力供应紧张时,核电厂的“表现也都非常好”。因此在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,核电的身份已经从清洁能源转为“保供能源”,在能源安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国际能源署8月发布的报告《核能和能源安全转型》也提到“今天的能源危机可能会导致核能复兴”。 一位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人士对记者透露,实际上,国家能源部门去年就在积极酝酿加速上马核电,但由于各种原因,去年“没办法一下批这么多”,今年综合考虑各种因素,再加上条件也成熟了,就相对集中地核准了两批新的核电项目。 各种因素综合下,中国核电今年重新起飞。赵成昆分析说,中国核电起步晚,早些年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,但现在,无论在自主三代核电技术,还是制造、安装、质量把控、工程管理等方面都居于全球前列,“整体技术力量很强,且大多数设备的国产率能达到90%左右”。因此每年开工6~8台机组,是根据中国当下核电能力做出的“一个比较客观和审慎的规划”。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核能总工程师、“国和一号”总设计师郑明光提供了一个更乐观的预测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随着工程进度的有效、有序推进,中国核电的总体制造能力大约可以“保证”每年同时开工12台机组,“未来,批量化建设核电就是必经之路”。 事实上,从去年起,核电的起飞就已见端倪。2021年3月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提出要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”,这是近十年来中国官方首提“积极”发展核电。赵成昆指出,“有序发展”就是要尽可能避免大起大落。 自1985年,浙江秦山建设了中国第一座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后,中国整个核电发展脉络一直起伏不定。1990年代以“适度发展”为方针,十年内批准了8台核电机组。2005年之后,从“适度”转为“积极”,随后五年内新开工30台机组。但到了2011年,日本福岛发生核事故,中国核电审批一度暂停,2019年~2021年每年平均新增核准机组只有4~5台。赵成昆认为,影响中国核电“有序发展”的不确定因素中,最核心的仍然是安全。 实际上,中国迄今未发生任何一起2级及以上的核事件。按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核事件的分级标准,4至7级为核事故, 等级越高,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越大。全球已发生的三起重大核事故中,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核事故为5级,1986年切尔诺贝利和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都是最高等级7级。 目前,全球核电技术已经进化到第三代,第四代仍在研发试验阶段,多种技术路线并进。第一代核电技术是以实验研究堆为主;第二代的主要发展阶段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到1979年以前,目前发生过事故的核电站技术均在二代以下;第三代是在充分认识、分析了重大核事故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,设计上主要围绕核电运行安全进行了一系列改进。 中国是继美国、法国、俄罗斯等国之后真正掌握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,代表性技术是“华龙一号”和“国和一号”。“华龙一号”是由中核和中广核自主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,首堆福建福清5号机组已于2021年1月30日投入商业运行并顺利并网,标志着中国的三代核电技术已跻身世界前列。 2020年9月28日,由国电投开发的“国和一号”(CAP1400)发布,CAP1400是在吸收消化国际先进的非能动技术基础上、通过国家重大专项自主研发而来,目前该技术尚未进入商用,位于山东荣成市的首个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中。另外,由华能主导开发的高温气冷堆已具备四代核电技术特征,首个示范工程已于2021年12月并网发电。国内其他四代技术路线仍在研究中。 三代技术能否让福岛事故不再发生? 专家指出,三代核电技术和二代的主要区别,关键是在安全性的提升上。衡量核电站安全性的一个关键指标是,反应堆每堆年可能发生堆芯熔化的概率。堆芯是核反应堆的核心结构,如果堆芯内余热无法及时有效导出,就会造成堆芯熔化。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福岛核事故中,先是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发生里氏9.0级地震,继而引发浪高达14~15米的巨大海啸,这些极端自然灾害迅速造成核电厂失去动力电源,冷却系统随之失效,使堆芯内热量无法导出而发生熔毁,造成了大量放射性物质外泄。 “三代核电对堆芯熔化频率的基本要求是小于等于1×10-5,即十万分之一遇,二代核电的一般是1×10-4,而‘国和一号’机型CAP1400的堆芯熔化频率可以做到小于4.02×10-7,安全性比国际上对第二代核电的安全要求高100倍以上。”“国和一号”总设计师郑明光说。 三代与二代技术相比另一个重大技术进步是引入了“非能动安全系统”。传统的二代核电一般采用能动安全系统,堆芯的有效冷却是通过泵将冷却水注入反应堆中。这是一套以电力为支撑的机械装置,事故发生后可自动启动。如果一旦失去动力供应,堆芯冷却功能就会丧失。福岛核电事故中就是如此,由于只有能动安全系统,电力和备用电源都失效后,整个安全系统随之瘫痪。 为解决这个问题,美国西屋公司的工程师们研发出一套不依赖动力电源,而是依靠重力、温差、密度差等驱动的非能动安全系统。郑明光说,“国和一号”的安全设计就是全面采用了高可靠的“非能动”理念,一旦发生事故,被置于高处的应急水会在重力作用下流到堆芯或安全壳表面,自动冷却堆芯并导出安全壳内的热量。 郑明光进一步解释,非能动系统利用的是大自然的客观规律,比如水往低处流,水热之后要自然蒸发,热蒸汽遇冷会发生冷凝等。因此相对来说,非能动比能动系统在极限情况下更可靠。 并且,“非能动”系统是被动触发,事故发生后72小时内都无须人工干预,给了操作人员足够“宽容时间”去了解核电厂所处状态。同样吸取福岛教训,第三代核电的安全系统都强化了对极端事件的包容性,为应对9.0级地震这类“黑天鹅事件”做好准备。 赵成昆总结,各国从福岛事故中得到的最重要经验,就是必须通过防御措施保证一直有“可靠电源、可靠水源和可靠的现场操作人员”。当严重事故发生后,只要这三方面能“控制保障得好”,就可以有效防止堆芯熔化,“后面的安全环节就好办多了”。 在核安全领域,最重要一个概念就是“纵深防御”,对可能的核事故层层设防,前一层次失效时,后一层次将加以弥补或纠正,不同层次防御间要尽可能相互独立,以避免共同失效。福岛核事故堆芯熔毁后,如果有更好的应对措施,运营者能做出更及时的反应,最终可能不会导致如此大量的泄漏。 为了满足这一点,三代核电站进行了一系列改进,比如采用了大容量的双层安全壳,这是核反应堆的最后一道屏障。“即使真的不幸发生了堆芯熔毁,也可以让这些放射性的水封闭在安全壳内,不进入到环境中去。”赵成昆解释。 郑明光说,在设置了完整严重事故与堆芯熔毁应对措施之后,中国的先进三代核电技术已经“不再存在福岛核电堆芯融化后放射性释放的场景或可能性”。 前述接近国家能源局的人士强调,一个核电站的安全运行,与多种因素有关,除了安全性设计之外,还需要有质控良好的制造能力和高效的运维管理水平。 对核电厂的严格监管也是确保事故不会发生的重要前提。日本国会在福岛事故发生后的最终调查报告中称,根本原因是日本监管当局和东京电力公司间的关系错位,导致“监视、监督机制崩溃”,错失预防核泄漏的最好时机。事故发生前数年间,东京电力曾报告发现福岛第一核电站28次修改反应堆数据,同时,它还意识到要对核电站结构加固,如果海啸达到超设计基准,可能会发生堆芯熔毁和全面停电的风险。 中国民用核电站的监管由国家核安全局负责,随着“十四五”期间开工的核电机组不断增多,覆盖的机组类型(水冷、气冷)、技术路线也越来越多元。前述人士指出,未来核安全监管机构将面临“多堆型、多技术、多标准”的复杂局面,当下亟须扩充监管队伍、提升监管水平,并对每一种机型、技术更具针对性的监管,而非照搬国外标准。 影响终极核安全的“游戏改变者” 将目光从东部沿海地区的核电站移向西北地区:北山金庙沟村25号。在甘肃肃北县马鬃山境内,这里是中国北山地下实验室所在地,也是保障中国长期核安全的“最后一站”。 这是一片大西北典型的“无人区”,人烟稀少,常住人口只有一户牧民,王驹接受记者采访时,正是深秋十月,北山的36棵胡杨树已经全部染成了金黄,这是当地季节流转的唯一证据,这里连动物很少见到。但对王驹来说,这片荒芜之地是处置核废物的“理想场所”。 王驹是北山地下实验室总设计师、中核集团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副院长,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指出,核安全主要是解决两方面问题:一是防止核设施发生事故,二是核废料的永久安全处置。核电站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中,99%属于中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,经过一段时间,其放射性就会衰变至无害水平。只有剩下的1%属于高水平放射性废物(下简称“高放废物”),含有钚、镅、锝等放射性核素,放射性强、毒性大、半衰期长,需要上万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自然衰变到无害水平,如不能安全处置,将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巨大影响。 高放废物来源主要有两种:乏燃料(反应堆中核燃烧“燃烧”后产生的废料)和乏燃料后处理产生的高放废液及其固化体。王驹解释,美国、瑞典、芬兰等国出于处理成本等经济考量,将乏燃料直接埋入地下或长期封存。中国、英国和法国等认为乏燃料仍是一种资源,可以从中提取出有用的铀和钚,重新作为燃料循环使用。剩下的废液固化后装入特制废物罐中暂存,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贮存方式。 专家指出,中国积累的高放废物仍长期存放在地表,部分废物贮存时间过长,管理成本和安全风险逐渐增加,成为影响中国长期核安全的重要隐患。并且,作为在建规模世界第一的核电大国,随着“十四五”期间核电机组规模不断扩大,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也将持续增加。 对于高放废物的永久安全处置,目前,国际上经过了几十年的广泛讨论和验证,在提出“深岩层熔融处置”“深海沟处置”“太空处置”等多种方案后,最终形成共识:“深地质处置”是目前最安全可靠且技术上可行的方案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其为“游戏规则改变者”。 这种方案中,把高放废物深埋于距离地表深度约500至1000米的处置库中。处置库须在各种未来演化情景及不确定因素影响下,实现对有害核素万年以上的包容、隔离,防止有害核素对生物圈的不利影响,确保长期核安全。各国目前都规定,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对应的安全隔离期不得少于一万年。 中国从1985年起开始处置库的选址工作。综合评估甘肃、内蒙古、华东、华南、西南和新疆6个预选区后,2011年,国防科工局和原环保部联合召开专家评审会,最终选定的首选预选区,就是甘肃北山。2021年6月,北山地下实验室正式开工,这是中国首个高放废物处置地下研究实验室,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总体设计建造。至此,中国在确保长期核安全的战略问题上,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 北山地下实验室有两个主要的试验平台,分别位于地下280 米和 560 米深处,主体结构由三个垂直向下的竖井和倾斜的螺旋坡道相连,从三维透视图看,就像一个缓慢盘旋下降的螺圈。“螺旋坡道目前已经向下挖到460米深处,揭露出的岩石极为完整,与预测结果完全一致,螺旋斜坡道地下硐室的稳定性也非常好。”王驹说。 他解释,地下实验室并非最终处置库,不会埋入真的高放废物,只是一个“彩排平台”,通过研究为最终处置库的选址提供科学依据。目前的工作与建成处置库的工程目标相比,还相差较远,仍处于选址的前期研究阶段。按照国家规划,将在2040年确定处置库的最终场址,2050年左右建成并开始运行。“对于是否能遵循这个时间表推进,我总体上比较乐观。”他说。 “邻避效应”何解? 王驹分析,为了更好隔离高放废物,最终选址的确定要考虑两类因素: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。以北山为例,当地海拔在1500~2500米,长年干燥,年降雨量只有70毫米,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,地表水系不发育、地下水贫乏。“这样,渗透侵蚀到处置库的地下水就会极其稀少。”他说。同时围岩主体是坚硬的花岗岩,岩体完整、厚度可达2000米以上、渗透性极低,且地壳稳定,地震活动很弱。 另一方面,当地人烟稀少,也没有矿产和动植物资源可待开发,土地无更重利用价值,社会经济发展潜力很低。未来,还需考虑公众的接受程度。“北山仍是最有希望的一个预选地,不过如果处置库最终决定建在这里,核电站大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,运输安全将非常重要,这就涉及利益和代价的权衡问题。”王驹说。 实际上,关于高放废物地质处置,虽然目前在工程技术上具备可行性,但对其长期安全性的评估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。其中关键挑战,就在于需要处置的时间跨度至少在上万年以上,而且人类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。 “比如有很多科学和技术问题还有待解决:以现有的地表实验室条件研究废物罐的安全性,认为它抗腐蚀能力很强,但在一个深部地质环境里,经过了上万年的演化之后,其抗腐蚀性是否仍能得到保证?在上万年的时间尺度下,放射性核素又会以什么方式在地下水中迁移?迁移到什么地方?”王驹说。 除了技术痛点以外,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专家在2021年发表的论文《高水平放射性废物深地质处置法规标准探讨》中还指出,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制定相关法律法规,造成处置责任不明、体制机制不协调、顶层规划缺失、资金筹措与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,放射性废物管理严重滞后于核能发展。 众所周知的是,核电安全问题涉及利益主体众多,公众敏感性强,即使技术、管理、制度、监管等层面的问题解决了,最终制约中国核电发展的关键,仍要看是否能解决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”的“邻避效应”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2018年10月举办的“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”上说,在一些地方,中国核能发展遇到了难以被公众接受的窘境,主要原因是公众对核电的认识有限,未能很好地、客观公正地认识核电,甚至出现被误导现象。 这方面,芬兰、瑞典、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经验值得借鉴。芬兰于2021年开始建设高放废物永久处置库。作为全世界第一个拥有处置库的国家,其在选址阶段就向当地社区开放了办公区域,并对社区承诺,如果该地被选中,他们将获得否决权。等到项目审批时,更是创造了处置库所在城市七成以上民众支持的纪录。 处置库位于芬兰西部的奥尔基洛托岛,这个岛上还有芬兰五座核电站中的三座。这是一片平坦的土地,被松树覆盖,三边与波罗的海接壤。选址最终决定时,奥尔基洛托岛上的小型农业和渔业社区接受了该项目。与此同时,在距离该岛车程只有约20分钟的陆上城镇劳马,人口约 34000人,也对核安全表示了放心。 瑞典进度比芬兰稍慢一步,处置库于2020年获批。此前在建设地下实验室阶段,瑞典就把其作为与公众沟通的窗口并对外开放,每年约有12000人前去参观,其中包括瑞典女王。相反,美国早在1991年就确定在尤卡山建设处置库,但由于内华达州当地民众强烈反对,最终国会没有继续拨款,让项目搁置至今。 在王驹看来,“邻避效应”是一个信任问题,破解出路在于公开透明,“我们目前专门有一个课题组研究如何促进与公众的沟通,让他们更了解处置库建设的安全性与必要性。想让公众理解我们,首先就要做到两点:公开和透明,并且让公众参与决策。” 杜祥琬也建议,公众不仅是科普对象,还是参与主体,一开始就应参与立项的酝酿、沟通和论证,“参与进来不是开一个报告会,让他们当听众这么简单,必须制度化、法制化、组织化,形成一种机制。” |
中国一年10台机组获批,核电安全问题何解?
文章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 发布时间:2022-11-14
摘要:11月1日,大连瓦房店市红沿河镇及周边的两万多居民,首次感受到当地核电站“送来的温暖”。这一天,东北首个核能供暖项目在辽宁红沿河正式投运,以替代红沿河镇原有的12个燃煤锅炉房,据测算,项目投产后每年将
核聚变中粒子行为“出人意料”
2022-11-14
东电申请审查测定排海核污水中30种放射性物质的计划2022-11-14
为保障冬季用电,德国批准核电站继续运转2022-11-14
中国一年10台机组获批,核电安全问题何解?2022-11-14
中核集团“核蓄一体化”抽蓄项目主体工程开工2022-11-14
我国在建产能最大铀矿山 实现多项技术突破2022-11-14
张廷克:预计2025年 我国核电在运装机将达到7000万千瓦左右2022-11-14
中核集团:探索零碳未来 开创美好生活2022-11-14
我国又一地进入“核能供暖时代”2022-11-14
其他资讯
- 联合国气候大会聚焦落实承诺
核心阅读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,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备... - 中国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动力
“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,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,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... - 我国成功勘探发现首个深水深层大气田
中国海油19日晚发布消息,在海南岛东南部海域琼东南盆地再获勘探重大突破,发现了我... - ·中国经济“升温”预期增强
- ·多个世界第一!我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
- ·人民币成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
- ·国常会:狠抓政策落实推动经济回稳向上
- ·国务院常务会议最新部署!再退税320亿元
- ·王中林院士:能源转型需要颠覆性原创技术
- ·全球最大液流电池储能调峰电站接入辽宁电网
- ·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.3万亿斤以上,中...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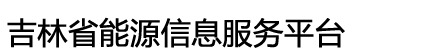
 吉公网安备 22010402000830号
吉公网安备 22010402000830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