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储能,光伏发电,光伏储能 8月27日,国家发改委、国家能源局发布“关于公开征求对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”风光水火储一体化“”源网荷储一体化“的指导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意见的公告”。征求意见稿指出,“风光水火储一体化”侧重于电源基地开发,应结合当地资源条件和能源特点,因地制宜采取风能、太阳能、水能、煤炭等多能源品种发电互相补充,并适度增加一定比例储能,统筹各类电源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运营,积极探索“风光储一体化”,因地制宜开展“风光水储一体化”,稳妥推进“风光火储一体化”。 向新能源转型不仅是世界各国的能源发展趋势,更是我国的既定国策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会议上庄严承诺,到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要达到20%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《中国新能源发展路线图2050》,到2050年,太阳能发电量将达到21000亿千瓦时,也就是说,光伏发电量要在2018年的基础上提高近11倍。要实现这个目标,储能将是绕不开的话题。 两类储能各不同 发电侧储能并不是因为新能源发展而出现的新事物,是各种类型的发电厂用来促进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的配套设施。从累计装机容量来看,目前抽水蓄能方式份额最大,但电化学储能因为其响应速度快、布点灵活等优点,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根据中关村储能联盟数据,2019年5月至2020年7月,全球新增发电侧电化学储能项目113个,中国新增发电侧电化学储能项目59个。目前,电化学储能已经成为发电侧储能应用领域的重要方式。 当前我国发电侧储能从用途上看主要有两类。 第一类是火电配储能。主要是保障发电厂具有一定的调频调峰能力,提高火电机组的运行效率和电网稳定性。同时,在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深度挖掘火电的改造空间,拓宽火电的盈利方式。火电配电化学储能在我国已有广泛应用,山西、广东、河北都有发电侧火储联合调频项目。 第二类是新能源配储能。相比火电,风电和光伏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很大,为保证电力系统的整体平衡,往往造成部分地区“弃风弃光”现象。2019年,在新能源发电集中的西北地区,弃风率和弃光率仍然很高。例如,新疆的弃风率和弃光率分别是14%和7.4%。电化学储能作为新能源的“稳定器”,能够平抑波动,不仅可以提高能源在当地的消纳能力,也可以辅助新能源的异地消纳。 当下面临五大难点 尽管电化学储能在发电侧已经有很多示范项目,但在应用方面仍然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。在政策和运营层面,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: 一是传统电力市场给储能留下的空间不大。发电侧储能的收益直接来源于电力市场,因此电力市场的总体运行状况对储能的发展有着直接影响。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,截至2020年1月,我国电力装机总量在20亿千瓦左右,2020年1~6月全国总用电量为33547亿千瓦时。这说明我国存在电力生产过剩的情况。同时,我国还不断有用于调峰的火电(燃气机组)、新能源机组上马,装机总量不断上升,导致储能的作用难以体现。 相比欧美国家,我国的电力设施很多都是近些年修建的,基础设施更为“坚强”,具有相当的容纳能力。这就使得电网对储能所提供的辅助服务没有强烈需求。在美国,由于新建电厂的审批控制以及电网的老化,电力公司急需储能来平抑波动和满足扩容需求,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储能的大量需求。 二是储能作为辅助服务市场主体的资格不明确。 储能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提供的辅助服务上,因此辅助服务市场的规制对储能的收益有着决定作用。在发电侧,电化学储能是作为发电厂机组的辅助设备运行的。作为机组的附属设备,电化学储能没有辅助服务市场独立的经营资格,由此导致电化学储能的收益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。由于很多发电侧的发电和储能是分开管理的,当政策变化时,由于没有主体地位,储能运营商可能没有多少谈判的能力,收益可能会进一步降低。 因此,发电侧储能的主体地位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目前,某些地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。例如,福建晋江的独立储能电站就拿到了“发电业务许可证”,以此为切入点让独立的发电侧储能进入电力市场。但即使如此,储能在市场中的身份和交易机制也不够健全。 根据2020年6月国家能源局福建监管办公室发布的《福建省电力调峰辅助服务交易规则(试行)(2020年修订版)》规定,独立储能电站的充电可以“采取目录峰谷电价或者直接参与调峰交易购买低谷电量”,放电时则“作为分布式电源就近向电网出售,价格按有关规定执行”。这就导致在调峰方面,储能的调峰收益更多是由计划和磋商决定的,充放电价的不明确给储能的收益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。即使在青海、湖北这样将电储能交易纳入调峰市场的省份,也只规定了储能电站充电时的交易机制,关于放电依然是“按照相关规定执行”。 除了以上的困难之外,由于储能在调频方面具有极好的性能,因此,储能的主体资格还面临着来自辅助服务市场内部成员的阻力。 三是辅助服务市场机制不完善。由于储能本身并不创造电能,因此储能的收益只能来自提供辅助服务的收费,而我国的辅助服务市场机制尚无法满足储能商业化运行的要求。 我国目前的辅助服务机制要求发电侧“既出钱又出力”,也就是要求并网发电企业必须提供辅助服务,同时辅助服务补偿费用要在发电企业中分摊。通过从这些企业中收取一部分资金,加上一部分补贴,形成一个资金池。调度中心根据各辅助服务主体的绩效打分,来决定发电企业能从这个资金池中收回多少份额。 以2019上半年为例,我国电力辅助服务总费用共130.31亿,占上网电费总额1.47%。其中发电机组分摊费用合计114.29亿,占87.71%。如此制度设计就决定了辅助服务市场基本是一个“零和博弈”,辅助服务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。 因此从发电厂的角度来看,如果大家都通过配套储能来提供辅助服务,那么会出现发电厂收益并无变化而成本却提高很多的问题,进而使发电厂缺乏安装储能设施的动力,这也是造成储能项目多是示范工程的原因。即使宏观政策支持发电侧储能的发展,这样的辅助服务机制也很难给发电侧提供正向激励。在辅助服务市场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,储能的收入来源十分单一,很难达到商业运行的要求。 四是储能标准缺位。我国电化学储能行业近几年才初具规模,储能电池还没有国家层面的标准规范。在没有确定标准的情况下,储能电池的回收和梯级利用也难以有效实施。例如,部分地区在探索退役动力电池应用于储能领域,但储能电池的要求和动力电池有很大不同,错误的梯级利用不仅带来效率方面的问题,更严重的是存在安全隐患。而且,相关法规的确缺失,可能会导致储能电池出现像铅蓄电池一样的回收乱象。 五是运营问题。储能的运营问题主要在于储能的容量和成本。现有的发电侧储能项目容量一般在10~200兆瓦时之间,多数不超过100兆瓦时,考虑到未来新能源装机容量越来越大,这样的储能规模显然难以充分助力新能源消纳。现有的电化学储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轻松增加容量,当然,随之而来的安全问题也需要高度关注。 电化学储能的成本问题更是储能难以大规模投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以光伏发电为例,在西北等光伏资源丰富地区,虽然已经可以做到平价上网,然而配套储能设施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或者补贴政策,发电成本就会大大提高。再考虑到设备的衰减和老化问题,成本的回收会更加困难。 因此,目前在没有明确且足够的政策补贴时,电化学储能难以大规模地投入使用。 未来需要四大支点 尽管电化学储能有以上的种种限制,它的前景却是明朗的。随着我国能源转型以及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,电化学储能未来的定位会越来越清晰,应用的价值也会越来越得到体现。 第一,提高消纳能力。 未来新能源发电会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。与此共生的消纳市场给电化学储能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一方面,新能源配储能可以帮助解决新能源在当地的消纳问题,储能能帮助风电和光电摆脱“垃圾电”的影响。更重要的是,由于我国的风、光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北部,而需求负荷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。如果未来要更多地依靠新能源,那么电力的跨地区转移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。这也是特高压进入我国“新基建”计划的一个原因。通过特高压,大量的新能源电力可以转移到沿海区域而中途没有过多的损失。 第二,扩大电力市场容量。 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,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,未来新电厂的建设会放缓。同时,用电需求仍然会不断上涨。考虑到电网的经济性,相比于建设新的电厂,未来更多的关注点会集中在电力系统的优化方面。例如通过合理的削峰填谷、需求响应来解决电力市场的扩容问题。 在这方面,电化学储能由于其快速的响应能力,在未来的电力容量市场中具有相当大的潜力。如果通过EMS(能源管理系统)能让储能在容量市场充分发挥其作用,那么扩容问题能得到部分解决。 第三,促进市场价格机制形成。 本着“谁受益,谁承担”的原则,目前的辅助服务成本分配方式不尽合理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在不久前发布的《关于做好2020年能源安全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》中指出:“进一步完善调峰补偿机制,加快推进电力调峰等辅助服务市场化,探索推动用户侧承担辅助服务费用的相关机制,提高调峰积极性。推动储能技术应用,鼓励电源侧、电网侧和用户侧储能应用,鼓励多元化的社会资源投资储能建设。”如此,让所有受益的市场主体,都来承担辅助服务成本,辅助服务的价值才能在市场中得到较好的体现。发电侧储能将有更大的积极性在应用方面进行尝试和投入,电力用户也会根据市场价格进行需求的自我调整,从而提高电力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。 第四,对生态环境影响小。 在不同的储能方式之间,电化学储能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有其优势。以抽水蓄能为例,一般需要在山地环境下建设上下水库、安装大型发电机组,电站建设运行可能会对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。而电化学储能在选址上没有抽水蓄能那么多的地理限制条件,且占地面积小很多。以晋江储能电站为例,总占地面积10887平方米,以围墙内面积计算,全站能量密度为42.5千瓦时/平方米。在电化学储能应用和回收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,预计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会远小于抽水蓄能。 (尹海涛、瞿茜均供职于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和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,李新钰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) |
发电侧储能的难点和支点
文章来源:能源评论?首席能源观 发布时间:2020-09-03
摘要:8月27日,国家发改委、国家能源局发布“关于公开征求对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”风光水火储一体化“”源网荷储一体化“的指导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意见的公告”。
高亚光委员:尽快出台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强制性标准
2020-09-03
这家公司正式纳入宁德时代供应链体系!2020-09-03
新能源汽车行业动力电池数据跟踪:磷酸铁锂产量增幅较大 锂价格大幅增长2020-09-03
碳酸锂突破50万/吨:别贪婪,该恐惧2020-09-03
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技术发展趋势研判2020-09-03
储能市场处于爆发前夜2020-09-03
远信储能与云南楚雄州姚安县签约年产2GWh锂电池储能装备 制造项目2020-09-03
福特中国也考虑用磷酸铁锂刀片电池?2020-09-03
新面貌,新征程!西子洁能(原杭锅股份002534)全新官网重磅上线!2020-09-03
其他资讯
- 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
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今天(3月3日)下午举行,新闻发布会采用网络视频... - 我国对欧投资保持逆势增长 2021年中欧...
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,2021年,尽管面临的形势比较复杂严峻,但是中欧之间的经贸... - 中国两会的世界期待
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。在新冠疫情持续不断、全球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、国际格... - 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在京举行
- ·国家发改委:坚决淘汰煤化工领域落后产能
- ·两部门:健全能源供应保障和储备应急体系
- ·全球天然气价格暴涨,中国如何打赢今冬“冷战”...
- ·全球制造业PMI连续下降 全球经济复苏动能持...
- ·习近平出席2022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并发表...
- ·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领域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...
- ·国家能源局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印..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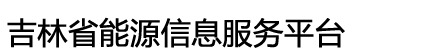
 吉公网安备 22010402000830号
吉公网安备 22010402000830号